长沙自建房坍塌后:被改变的街道和无家可归的工人(组图)
「房子倒塌时,韩宁政想的第一件事是“黄码的他可能要露宿街头了”。」

2022年5月29日,湖南长沙,自建房倒塌现场。摄:Yang Huafe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53条生命,消逝于4月29日湖南省长沙市一栋自建房的坍塌事故中。
事发前一天,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迎来一场暴雨,当天降雨量超过50毫米,雷雨交加,大风席卷过金山桥街道。当天天气预报称致灾风险较高,提醒居民注意防范。两周前冰雹也刚刚光临过此地。
旁边是一座城中村,内部的街巷在地图上没有名字,当地居民和长沙医学院(以下简称“长医”)的学生习惯把这里的街巷称为后街,以一街二街三街作为区分。其中,后一街与长医离得最近,步行不到三分钟,街道的营业额和学生密切绑定在一起。
雨停,新的一天伊始。自2022年2月20日开学起,长医施行封校管理,直到4月20日才解封。算上寒假,三个多月略为冷清的街道涌进了被封两个月的学生,他们穿着薄外套三三两两地走在后一街上。
热闹的气氛在12时24分被一栋老式自建房的倒塌打破。倒塌发生在一瞬间。“轰”的一声,紧接着一阵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秒,以后一街为中心,辐射几百米内的人的生活轨迹就此改变。
一名长医的学生称事发当天,十几名学生在倒塌楼的杨国福麻辣烫店里聚餐,那是学生们最常去的场所。在微博超话上,关于被困学生的祈祷和回忆从没有停止过。
一名食堂员工中午下班的时候从后一街的小门出来,目睹了一整块广告牌的掉落,灰尘弥漫在空气里,“整个都是乌烟瘴气的”。有一个女学生满脸带着血冲出来,食堂员工刚要上前察看,就被救援人员清了出去。
根据当晚的初步调查,倒塌房屋系居民自建房,共8层,其中1楼为门面,2楼为饭店,3楼为放映咖啡馆,4、5、6楼为家庭旅馆,7、8楼为自住房。承租户对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结构改动。
事发前十六天,湖南湘大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曾对该自建房家庭旅馆(4、5、6楼)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后出具虚假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公司法人代表谭某及技术人员等5人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已被刑事拘留。

2022年5月4日,湖南长沙 ,救援人员于自建房倒塌现场运送一名幸存者。摄:Yang Huafe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逃生
这是韩宁政的健康码变成黄码的第十天。十一天前,他从广东虎门站坐高铁来到长沙。同样来长沙打工的发小告诉他,“只要来长沙,就是黄码待遇”。
他不信。来的时候拿了48小时的核酸证明,出长沙南站又做了核酸检测。住下的第二天,他按照流程去长沙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核酸,扫完场所码,黄码赫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此前,他从深圳出发去虎门,父母在虎门的电子厂打工。厂里因为疫情封闭,工人不能进出,三人没有见上一面。
黄码限制了韩宁政的自由,他只能出入那些不需要扫码的场所,不能去任何商场。
事发当天他一直睡到十一点,起床去便利店买了一根烤肠和一根玉米。回到家,本打算出门做核酸的他犯了懒,躺在床上刷了会短视频,嘴里啃着玉米,刷到第二个、手指往上翻的时候,耳机里传来剧烈的震动声,他误以为是隔壁办丧事的在放鞭炮——前一天早上他被炮声吵醒。 但韩宁政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向外看,发现对面的楼在往下塌陷。他以为是地震,迅速躲到桌子底下,震动声响了十秒。一直等到周围安静下来,他才小心翼翼地爬出来。
几分钟后,韩宁政推开门,浓厚的尘雾瞬间散了进来,脸上的眼镜被遮挡得严实,眼前一片白色。他戴上口罩,拿起手机冲了出去,只来得及穿上衬衣,连身份证也没带。
李志是在中午12点半跑下来的。六分钟前他正在被窝里睡觉,被一声巨响惊醒后翻了个身继续睡——前一天晚上他轮班休息,报复性熬夜到凌晨五六点才睡下。
房东打电话催促他立刻出去,李志拿了手机,睡衣里套了件褐色的绒面夹克,还没来及穿鞋,胡乱穿了双深蓝色的拖鞋就跑了出来。
房东清点好人数后,让大家四散离开。李志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他还不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住在这家家庭旅馆里。
韩宁政租住的旅馆是一栋自建房,确切地说整条后一街都是自建房,只不过他们的楼恰好在倒塌的楼的斜对面,也是唯一被波及的自建房。
二楼墙壁坍塌抵住了大门,老板娘在二楼午休,门被卡住,出不来。她焦急地呐喊。浓烟滚滚,韩宁政绕过碎墙,边咳嗽边把门打开,“等一下再出来,可能墙还会继续掉。”
楼里有两间门面,中间是进出的走廊,他们从楼梯下去,一楼的一部分成了废墟,老板娘心急如焚,指着废墟对韩宁政说老板就在里面。
韩宁政赶忙上前,在废墟上徒手搬开石块,和他一起的是一名长医的学生,还有闻讯赶来的警察,三个人不知道旅馆老板的确切位置,也没听到任何求救声,他们猜测老板已经被吓懵了。
灰尘几乎要掩盖掉所有人的视线,十多分钟的营救后,大家才发现老板的位置。旅店的老板四十多岁,是自建楼的主人,这间被殃及的自建楼,一楼是水果店和奶茶舖,二楼自住,三楼以上是旅馆。
韩宁政观察到出来的人只有4个,按照长租一天50的租金算,一天的租金也只有200。
被救出后,老板的左手不停地流血,嘴里念叨着腰痛,救护车已经赶到,警察把他背到担架上,送了出去。
韩宁政也想快点离开,起身没走几步路,一截砖块砌在一起的白墙砸了下来,有一个半拳头厚、十几斤重,他没来得及闪躲,断墙砸在了他的腿上。
他吃力地把碎块移走,扶着地再次站了起来,走到后二街终点的公共厕所洗了下伤口,没有去医院。
他大腿酸痛,走路一瘸一拐,但还坚持去做了个核酸。
未来五天,气温持续上升,太阳重新升起,乌云散去,像是恰好为假期准备好的天气,但有些人再也见不到了。

事发地附近街道被封锁。摄影:沐秋
“黄码的他可能要露宿街头了”
韩宁政稍作休息从北门混进了长医。大门前,他看见不少学生在那里嚎啕大哭。两人在里面的一家奶茶店坐了下来,扫了充电宝充电。
韩宁政对塌楼并不恐惧,因为害怕家人担心,也没有和他们提起过。直到现在,他的父母也只知道韩宁政来到长沙打工,并不知晓他经历过什么,甚至也没有关注过这起事件。
房子倒塌时,韩宁政想的第一件事是“黄码的他可能要露宿街头了”,他只记得老板和他说连做7天核酸就会变绿,但他连续做了11天,没人能告诉他应该怎么转码。
这是他第一次变黄码,半个月前,工厂里有“有一个屌毛,红码了,结果还继续上下班,整个厂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变黄”,他们连续做了一个星期的核酸。韩宁政逃过一劫。
一直到下午五点多,韩宁政有些冷,他有一个21寸的纯色行李箱,里面装了三套换洗的衣服。他特意带了两件厚棉衣,占了行李箱的一半的体积。
他起身,走到封锁线以外,想着能不能进去拿件衣服。他暗自庆幸自己下楼前买过早餐,回家后懒得脱鞋就倒在了床上——周围有很多人穿着拖鞋。
此时特警已经守住了每个路口,把整个后一街围得水泄不通,“能不能拿件衣服,”他小心翼翼地问巡逻的警察,对方回复他,不行,离这远一点。
晚上八点,李志站在后一街的警戒线外,焦急地等待着,踮起脚尖向里面看。前面三个人先后在警察的陪同下进去拿了行李了。
他头发盖着刘海,可能是没洗头的缘故,几缕几缕地聚在一起,显得有些油腻。他想去买几件衣服,但附近所有的门店都关了。他把双手交叉叠在胸前,试图让自己暖和一些。
其中一个进去的是他楼上的邻居,对方告诉他自己拿手机打手电筒,被警察喝止,“可能是怕我们拍照。”邻居猜测。
马上要轮到李志的时候,警察改口,称所有人都不能进去了。
得知因为黄码不能入住的消息后,记者帮韩宁政拨通了望城区防疫办的电话,对方先是表示文件上有48小时核酸就能入住旅店,称如果旅店不接收可以投诉。
又拨通110派出所,对方好心提供了一家华美达酒店,但是要300多元一晚——相当于韩宁政半个月的租金。
11点多,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包括12345市民热线,派出所报警电话等等,对方态度很好,但也表示只能转接到疾控。最后打了救助站的电话:
“病毒很狡猾的,核酸做一次、两次,甚至五六次都查不出来。”
“可是他落地长沙后现在已经做11次了,11次还不够吗?”
“他原先是怎么住进去?”
“本来没有变码,和你们报备之后才变的。我已经问过所有的旅馆了,都不能住。”
“旅馆都不愿意,我也没办法啊,那个东西(黄码)就是带着一种病毒你知道吗?”
“黄码就是带着一种病毒?”
“肯定是的啊。”
挂断。

2022年4月29日,湖南长沙,救援人员于自建房的倒塌现场工作。图:VCG via Getty Images
“加盖”成风的后一街
在长沙医学院后一街街头靠近雷锋大道的一端,有一家开了15年的杂货店,孙黎坐在柜台后面守店,时不时有人进来买走一瓶水或者一包槟榔。
从中午吃饭时一声突然的巨响,到现在门口的黄色警戒线和熙攘的人群,让她意识到“可能以后这里要大变了”。出事当晚,这家杂货店营业到了半夜。
2004年,孙黎嫁过来时,这里还是望城县的黄金镇,旁边的长医还叫湘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后简称“湘南医专”),“校园也只有几栋教学楼,大概两三千名学生”。靠近事发地后一街的校区,那时还是一片荒地,“都长着草”。
校区北门后面三条街,楼房没有现在密集。后一街已经有部分居民建好了小楼栋,后二街是附近政府机关的职工楼,后三街则是随着2012年左右废旧大市场的建设盖起了楼房,“这边民房的房龄都不太高其实”。
生机是从长沙医学院的落址、扩建迸发的。2001年,长沙医学院前身湘南医专本部搬迁到望城;2005年,其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长沙医学院,学生人数扩招。靠近后一街的校区修建起实验室、体育场,学校北门在后一街的街头。
随着2011年望城撤县设区,归属长沙市;到2012年,镇改设为街道,这片被细分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
和其他大学的小吃街一样,这里成为了长医学子的小食堂,主营小吃的店面成为街道主体。不少学生下课后,会从学校北门出校来后一街吃饭。
要么是山要么是草的荒地,形成了以长沙医学院为中心,商业区在四周分立的格局。而且离长医越近,租金越贵。相隔几米的三条街,租金截然不同:一间门面房(如一间奶茶店),后一街一年租金十万左右,后二街一年3—5万,后三街大概一年一万。在后一街上,离长医北门越近的店,租金越贵。
多位周边居民及店家向端传媒确认,后一街存在严重的自行隔断和违建加盖的现象。一名餐饮店老板告诉端传媒,有屋主将阳台切割成了一个门面,还会将旅馆里的房间隔断成几间,一个月收五六百,“能多分一间是一间。”
根据当地初步调查显示,倒塌的自建房2012年建为6层,2018年加建到8层。加盖就像叠罗汉一样,先加至6层,又在楼顶搭上两层蓝色的棚院,以至于当地居民们对于倒塌楼的层数众口不一。为了方便顾客上下楼,房东还修建了一部电梯。
大量自行违建的背后自然是经济上的考量,上述加盖的阳台不到五平米,一个月的租金有2800,“多盖四五个这样的门面,一个月收入就多一万块的收入。”
后三街一家韩式料理店的老板介绍,她所租住的店面一个月只要一千多一点,而同样大小的店铺在后一街租金要上万。而红火的店铺在巨额租金以外还要支付转让费,有的转让费就高达二三十万。
根据《看天下杂志》报道显示,有曾经租住在后一街店铺的受访者称房东们开出的租金一年比一年高。第一次续签时,房租从七万五涨至十万八一年,涨幅近50%。而四年前签租赁合同时,房东就曾提出要从转租中收取一笔三万八的转让费用。四年换了五个老板的现象有了合理的解释。
这里的店铺“租不下去的就走了,走了又有人来,来了又有走的”,孙黎待了十多年,熟人也并不多。
林勇是长医食堂的员工,负责做快餐,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在食堂上班,赶到现场的时现场已经被完全封锁。住在后一街的五年里,他对价格的变化并不敏感,只知道旅店的月租涨过100,其他事情一概不知。
他告诉端传媒,事发前,二楼餐饮店的老板提到过墙壁有开裂的情况,但屋主要求五一之后再重新装修,“结果没等到五一就倒了。”
在后一街开卤粉店的大叔,租了一间后三街的门面来住,以此减少创业成本。但疫情以来,原本还能赚钱的生意,变得入不敷出,“现在是从网上贷着款,一点一点还”。
在他住的房子里,只有床、桌子、灶台这些简单的家具,生活存续在一种临时性和不安稳的状态中。楼倒塌后,后一街、后二街的店铺全部被关停清场,大叔连忙搬出了一个不锈钢盆,里面装着生鲜肉类。
“也不知道那些冰箱里的、水池里留着的菜会怎么样,但没办法,人家连命都保不住了。”

人们在警戒线外围观。摄影:任弯弯
“清人”
在政府网站上,有关金山桥街道的板块停在了4月29日。
馨怡家庭旅馆的吴老板,是在中午事件发生后接到“清人”通知的。后一街断电断水,他被告知安置房和老小区将被统一关停,公安局上门将识别身份证的机器收缴。
一名在3千米以外的旅店老板也向端传媒证实,事故发生不久,他们同样被强制关停,不允许接客,“我们房子明明没风险的,但也没办法。” 不过,还有一家旅店老板称可以提供住宿,80元一天,不用登记个人信息,但他嘱咐不要在其他平台上下单,“昨天派出所来查了两次,今天还没来过。”
吴老板的旅馆里有九间长租房,其中一间的顾客打给他问怎么办?他只能无奈地说自己也没办法,他听说有些房东自己都得睡大街了。
“倒塌的这个房子赚得太狠了,自己加装两层就算了,还挖了地下室。”他语重心长地说。后一街所有房子都是十几年前一起建的,现在不管是住建局、公安局,都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如果发生第二次,可能连市长都得撤下来。”因此,他初步估计整个望城区的旅馆将至少关停几个月、半年之久。
李志发现能找得到的家庭旅馆都被告知暂停营业,能问到的宾馆一天在200以上,“一点也划不来”。附近的网吧也全部关停。身边能够求助的朋友都在学校宿舍里,而事故发生后宿舍开始严禁出入,他没有办法,扫了辆共享单车,骑了15分钟,去了2公里之外的网吧通宵。包夜三十元,一直到早上八点,因为声音嘈杂,他一直睡不着,“基本上睡不着,睡一下就起来。”
一家烧烤店的店长称,因为后一街停摆,常去的菜市场关门,其他菜市场提供不了足够的货,很多菜品都短缺,暂时做不了。
零点过后,崭新的日期。整个街道弥漫在哀伤的气氛里。天气转冷,韩宁政本来想去网吧凑合一晚,但是想到网吧也要扫码,最近的网吧离这也里有1公里,只好作罢。
预报的雨水按时下起,穿着外套还是冻得瑟瑟发抖的他跑到警戒线以外的一家饭店门前,不好意思进去,搬了个椅子坐在门口。
门口有一个大叔,两人攀谈起来。对方说着长沙话,韩宁政要仔细听才能勉强听懂,一直到三点多店里的人群走空,大叔叫他喊进去休息,他才知道对方是店里的老板。
老板告诉他,“本来4点多要关门,但今晚要通宵营业了。”5点多,老板娘来接班,看到外面还有人影,把窗户拉开,让他们到里面来避雨,三个学生模样的人进来,一进门就找了桌子趴着睡下。
两波人没有过交流,各自趴在桌子上休息。韩宁政一直到早上8点半才睡着,直到11点多饭店来人,他才醒来。醒来以后,他本能地想去做一次核酸,走到目的地,发现专门给黄码人员做核酸的站点11点半就下班了。
他又困又饿,看到附近有个旅馆,想着冒个险、碰碰运气。厄运总算没有继续笼罩在他的身上,旅馆老板问他要身份证,他说自己的东西都在倒塌的公寓里。
老板没有继续“为难”他,也放了他一“码”。只让他在本子上登记个人信息。旅馆一天要80元,韩宁政身上剩下的钱只够订上三天。
如果没有疫情,韩宁政此时可能还在深圳的电子厂里做着熟悉的手机中板。
2018年,韩宁政高中辍学后,跟着村里人去了表哥的电子厂打工。那一年,他在深圳辗转,每一份工作都做不长。
疫情改变了这一切。2020年,整个深圳的工厂因为疫情按下暂停键,韩宁政和父母在邵阳老家等到四月才去深圳。他又回到了表哥的工厂里。 韩宁政所在的工厂以对外贸易为主,因为疫情停摆,原本两个月的淡季延长到了五个月。在韩宁政的记忆中,他有一个月超过10天没有上班,只拿了1000多元的工资。
在韩宁政已有的生活经验中,从海员学校毕业后当一名海员,是他最向往的职业,“就觉得还挺冒险的。”高二时,在父母要求下无奈辍学。韩宁政抗争过,但最后也觉得干脆算了,“家里面就我一个男孩子”。

事故救援现场被围上黑幕。受访者供图
不再确定的未来
为了防止周围人拍照,救援现场已经用黑色幕布遮住。除此之外,5月3日,长医一则紧急通知显示,11点07分,紧急通知宿舍楼一栋、九栋,以及十三栋南面的学生撤离宿舍,12点封宿舍楼。一名学生推测这是为了防止学生拍照,因为只有这三栋楼能看到救援现场。通知称让涉及马上回宿舍带着简单生活用品去教室,或者其他楼栋的同学宿舍,零点准时封楼。两天前,长医已经再次施行封校政策。
两栋宿舍楼有三四千人,政府按人头每天发了300元的补助,允许学生出校门居住,学生证上有宿舍楼号,特警在门口排查,只允许涉及的学生出门。
相比于学生,流散在此地的工人和店铺商家的未来,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李志是今年3月份才从邵阳来长沙的,在此之前他在深圳打工。去年年底回家后,过完年,深圳疫情爆发,先是工厂被封,然后是租住的城中村,最后是整个街道。
他着急赚钱,邵阳本地的工资又抵得可怜,一个月不到3000元,于是跟着朋友来长沙的电子厂打工。
岳麓区离这里有13公里,因为长沙医学院的几个朋友,他才选择租住在这里。九点上班,他每天早上七点半就要准时坐公交车。一顿午饭7.5元,从工资里扣,李志嫌弃肉少得可怜,宁愿多花几块钱出去吃快餐。 刚来不到一个星期,长沙疫情爆发,长医封校,他一个人独自上下班,还要忍受长时间的通勤。
自建房倒塌后,和他租住在同一栋楼的年轻人拼车回了老家,但他回不去:按照邵阳的政策,回去要隔离14天,回来又要隔离14天,相当于浪费一整个月,他耽搁不起。
韩宁政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应该留着房东的联系方式,因为他听说有租在这里的租户通过房东进去拿过东西,“还得找他退剩余的房费。”
但事实上,房东对此也无能为力。第二天顶着黑眼圈的李志又来到现场,他穿着拖鞋,脚趾有些发黑,像刚从泥土里出来一样。房东跟他承诺让社区的人带他进去拿行李,但一直等到五点多,才等来房东群里的通知:要等救援人员都走了之后,才能申请进去搬行李,具体多久还不知道。
工厂里有员工宿舍,但厂长为了防止把宿舍当成旅馆,随来随走,因此规定员工需要带着行李箱才能住进去。他挂念着他的被子,那是他刚来长沙找人借钱买的,“我就想把东西拿出来。”
今天拿不到行李,意味着五一假期里,他要在外面住四天,但“实在不行,也只能借钱住个宾馆了。”他失落地叹了口气。
住在长沙的十二个日夜里,韩宁政无时无刻不在找合适的工作,最初是觉得工资只有四五千,除去生活费,所剩无几。他本来想干脆回深圳,但是身上彻底没钱了,当务之急的一日三餐也有困难。他决定在长沙做到六月底,再回深圳。
搜救工作结束前的一夜,5月5日,凌晨两点,孙黎仍守着店铺,“给社区工作人员提供热水”,门前来了几位工作人员,开始测量、拉线,说上面接到通知,雷锋大道临街需要拉起铁板封起来。两米多高的铁板没多久就安装完成,靠着门店前的台阶,将外面的人行道一分为二。
孙黎上前交涉,希望能暂时留一个出口,好让他们把货物搬出去。“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和文件,就这样被封了”,孙黎一宿未眠。
这条街主营饭店和零售批发,不少店主的家庭情况和孙黎一家相似,上有老下,负担着一年六七万的房租。做餐食的店铺,冰箱里还存着不少冷冻生鲜食品,“一箱鱿鱼就是几千,上万的货物不处理也是纯亏损了”,在临街商户群里,大家都不知所措。
临街商户的微信群里,其他店主打电话给社区的熟人,说这条街的人员需要撤离、闭店三个月。孙黎一家六口住在商店的二楼,两位老人,两个小孩,租下一整栋楼养家糊口,“现在我每个月要还一万多的房贷,还要养孩子,闭店真的撑不下去”。
直至中午,孙黎仍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没有文件我是不会搬走的”。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韩宁政、李志、孙黎、林勇均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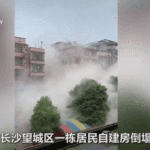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